|
偎着苔,倚着根,露半张脸,安闲地望。 这是我看到她的最初模样。那时我刚来到山顶,下了车,站在路旁,孤杉挂绝壁,云海耸青峰,瓦屋山孤高天外的气象果然不同。只一会儿,凛冽就从脚底透上来,似乎在提醒我,高处不胜寒,我只是游客,不是归人。 赶紧惶然后退。正局促间,忽然就看见了她。如同倚在农家柴门上的小姑娘,半幅阳光打在她绒绒的脸上,半睁半闭的眼眸,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慵懒。这份闲适感染了我,那一刻,我的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俄而,一只松鼠在枯枝上飞掠而过,几道折痕,一小片风。小姑娘一抬头,两眼一时如清潭一般,天光云影在眼眸中荡漾,也在我的心中荡漾。我忍不住朝她走去,正想和她打招呼,她却倏地从柴门里跳出来,珠玉般的笑声,一路撒花飞影叮叮当当远去。 我不禁有些怅然。身边的游人都忙着拍照,要留住她迅疾的倩影。我没有拍,我知她是留不住的,留在相机里的,只有她嫌弃的目光。 正叹息间,一块铁黑的大石阻了她的去路。她惊得一跳,珠玉的笑声就溅起来,成了碎末,洒入一旁的小竹丛里。竹丛下面是苔藓,苔藓下面是细沙,都是清洁之物。碎末沥过苔藓,沥过细沙,又转回来,汇入一个水凼之中。但她分明对这一阻碍有些不满,水面一两粒透明的水泡,装着她的怨气。 我忍不住笑了,大步向她走去。毕竟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当她跌跟斗时,正需要我的安慰。我双脚踩上湿漉漉的白石,蹲下来,伸出双手。我要掬一捧,让她感受到我手心的温暖、宽厚与耐心。却不料,我的手指伸进水里的瞬间,忍不住便猛缩回来。仿佛碰到了一团火,一团寒冷彻骨的冰火,尖刺一样直往我的肌肤里扎。 她是惊恐?是拒绝?还是恼烦? 我站起来,摇摇头,没入熙熙攘攘的游人之中。我用摇头掩饰我的尴尬,我再用没入人群的方式,掩饰我的虚弱。 从瓦屋山顶往下,木栈道穿行于绿竹青枝间,盘曲环绕,时隐时现。木栈道上有深深的横纹,防止打滑;两边还装有扶手,供人搀扶。木栈道穿行一段,便往旁边逸出一个凉亭,那是给游人小憩的。可喝茶,可吃饼,也可吹笛。 饶是这样,往下走依然是一件苦差事。膝盖承受着巨大的考验,关节磨损、乳酸堆积,都在消磨着我看花看草的闲情逸致。走到最后,全部的意念就集中于一件事:如何更轻松地让膝盖弯一弯?如何让脚掌稳稳落上下一级台阶? 也不知走了多久,转过一个湾,正喘息间,忽又遇见了她。 自山顶一别,我没入人群,她没入荒草,彼此再也不见。没想到,出其不意又相遇了。她没有路,她从山顶荒草野藤中破空而来,在木栈道旁的乱石苍根间肆意冲涌,冲得水花四溅,涌得潮头叠起。此刻的她,如同一个侠女,地上乱石丛生,脚踩凌波微步。她的身姿是流线型的,她的快乐也是流线型的。 或许,正是无路,才练就了这不管不顾的气魄和欢快豪迈的气概。 我站在木栈道上,伸出手,试图和她一握。但她只给了我一粒小小的水珠。那水珠在我手心呆站着,瞪着惶然的圆鼓鼓的眼,似乎正埋怨我为何把她留下。我不敢看那眼,我甩一甩手,把水滴甩入溪水之中。 瓦屋山是一座平地隆起的高山,山顶平整,四周都是绝壁。原先只能坐索道上下,但近日却在绝壁上新修了一条栈道,游人得以涉足这亘古未到的绝壁。瓦屋山的客人,也因此天天爆满。 下山时,我也去了绝壁栈道。绝壁栈道极长,远远望去,如苍藤缠腰。站在栈道口,有人忍不住大声啸叫。我默默拿出导游图看,导游图显示,走完栈道,得花三个半小时。望着从栈道口冒出来的白汽腾腾的游人,我明白这三个半小时意味着什么。 但我还是得往下走。和乳酸堆积斗争,和疲惫恐高斗争。战战兢兢刚走过一段,眼镜片就模糊了。我以为是脸上的蒸汽所致。摘下来擦一阵,戴上却又再一次模糊。仔细一看,才发现栈道外,竟然悬挂着一条瀑布。仔细一瞧,便能看到那悬垂而下的细细珠帘。风一吹,珠帘便散成一片薄纱,在空中慢慢卷漫着,如一支乐曲,又似一段舞蹈。 我侧曲身子,索性把脑袋往纱雾里伸。我和她都是从瓦屋山顶下来的,我一直顺着栈道走,早已筋疲力尽,胆战心惊。她却展示着自由的姿势和美妙的韵律。我要和她在一起,我要让我沉笨的身子飞起来,让我拘束的精神飞起来。 只是可惜,导游过来,提醒我危险,把我重新拉回栈道之中。 终于,我们来到瓦屋山脚下。眼前一面平湖,一望空阔。 接下来是游湖。我们穿上橘黄的救生衣,坐到一条船上,驶入湖心深处。望着波光粼粼的平湖,我心里很是感慨。那时候她还是个青涩小姑娘,没想到短短一段路,却已成长为一面大湖。还展开宽阔的胸怀,用大方之姿拥抱我。而我,即便走入她怀中,还得穿救生衣。为了便于救援,救生衣还是橘黄的——这是一种与青山绿水完全不协调的颜色,仿佛荷叶杆上福寿螺的虫卵,仿佛一颗不消化的锈钉。但我又不能脱掉,这是最起码的安全保障,最起码的文明意识。 我问导游,湖水还是很清冷吗? 导游笑着说,冷着呢!夹骨头的呢! 我默默退回船舱。是的,她的性子是不变的。她虽然长大了,虽然展开了宽阔怀抱,却始终用清冷之姿,表达着对我们的警惕和拒绝。 或许,她的姿势是对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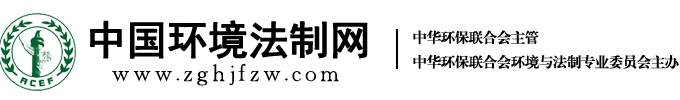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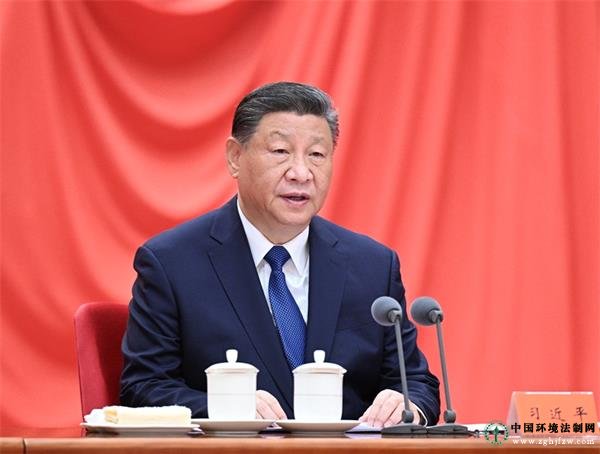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