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夕阳慢慢浸入河底,牧羊人驱赶着羊群在河边流过,翻腾起一场小型的带着膻味儿的“沙尘暴”来。祖父挺了挺腰板儿,背着粪箕子,从泛着金光的二十孔桥上挪着步子。河边洗衣服的妇女,挽着裤腿,将水里的被单子摆了一遍又一遍,水里的余晖也跟着洗了好几遍。 这条河是泗河的支流,它没有名字,或者说它的名字是因为一条横亘在河上的“桥”而得来的——二十孔桥。 然而二十孔桥并非是渡人的,而是渡水的,所以二十孔桥亦有另一个名字:红旗渡渠。 红旗渡渠 渡渠,亦叫渡槽,是一种输送水流跨越河渠、溪谷、洼地和道路的架空建筑物。 这是百度词条对渡渠的解释与说明。这么看这些落在纸上、浮于屏幕上的文字好像是再普通不过了,许多记录在案的渡渠也寥寥无几,但这些简练的文字堆砌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劳动人民用血和汗凝集起来,用肩挑背扛修建起来,用无数个日夜磨出来的伟大的水利长城。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抗旱排涝,解决用水问题和泄洪问题,全国大举兴修水利工程。修渠引水,自然是工程中的重中之重。泗水县大多数乡镇多山多丘陵,地势复杂,为成功的引水灌溉,修建了太多的水渠和渡渠。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干渠。 北干渠位于泗水县北部,横跨多个乡镇,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灌溉和泄洪作用。北干渠沿线有很多渡槽,其中现存的规模较大、工程较为完备、比较著名的有三大渡槽。其一是位于华村镇(原大黄沟乡)百家旺村、东陈村的“愚公渡槽”;一个是星村镇张家庄村蒲山脚下的“换新天渡槽”。其余渡槽还有泉林镇柳河峪的“引泉”渡槽,高峪镇的“争光”渡槽等,但都不属于北干渠了。红旗渡渠,自然也是北干渠渡渠其中的一个 ,只不过与其它渡槽相比,仿佛就显得藉藉无名了。 红旗渡渠坐落在今星村镇北百顶村北大队北边,东西走向,横跨泗河支流,总长80多米,高8米左右,宽4米左右,渠深约3米。一共二十个桥洞,都是一般大小,采用石砌拱券工程。渡渠正面镌刻着四个行书大字“红旗渡渠”,朱红的红漆脱落,露出原石本色,辨别起来稍有些吃力,但仍能感受到字体遒劲有力。沿着北大沟向东延伸便可与张家庄村的“换新天”渡槽相连。值得一提的是,红旗渡渠与换新天渡渠的名字,都能够在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里找到。前者藏在颔联“红旗卷起农奴戟”里,后者则出自颈联“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两座紧紧相连的渡渠,名字也在毛主席的同一首诗里紧挨着。我想,这既是对毛主席敢于与恶劣环境作斗争的精神之传递,也是独属于泗水劳动人民的浪漫。 提起红旗渡渠来,我不免想起我的祖父。 我总是记着在一个傍晚,祖父农忙归来,蹲靠在红旗渡渠渠头的石块上歇息。月亮悄悄从远山爬上天幕,照得河水越发的黑,只能隐约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新修的水泥路与红旗渡槽却被照得像极了静止的河水一样,发出了月光一样的白。祖父将幼时的我搂在怀里,一边卷着旱烟,一边和我讲着脚下这座渡渠的故事。 1977年,全国爆发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庄稼几近枯死,土地龟裂,据晋、冀、鲁、豫、陕、苏、皖等地统计,受旱麦田可达1066.67万公顷。其中鲁南地区遭遇了秋、冬、春三季连旱,泗水县政府为抵御旱灾,红旗渡渠同着北干渠开始修建,由当时的高峪公社主要负责,联合其他公社各个生产队出夫、出物资上堤修渠。祖父那年三十岁出头,正值壮年,自然也成了出夫的一分子。 祖父吧嗒着烟说,那时候整个大队北边流着两条河,一条是河谷里往南流的河水,另一条是河堤上由无数杆红旗组成的红色潮流,河水川流不息的汇入泗河,河堤上的红旗也在党的春风里不分日夜地飘扬着。 我昂起头来问祖父,那红旗不会累吗? 祖父好像很诧异我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可是又忽然明白了,小孩子怎么会有什么概念。他摸了摸我的头,歪着头笑着跟我说,红旗怎么会累呢?沐着春风的红旗是最有力量的。 祖父上过学,能写得一笔好字,也曾在大队里做过会计,自然能够说出这样有深意的话来。他说话时总是呼出一股旱烟味,衣服上也被熏得有股烟味,是一股汗味夹杂着淡淡的烟味。我很喜欢这种味道,不由得贴近祖父的身子,扣着祖父手上的老茧问,那你们累不累? 祖父的语气平淡得像是脚下的河水一样说,累啊,怎么不累。吃住全在堤上,饿了啃nia宁(音。泗水方言,指煎饼),渴了喝河水,晚上铺了盖体(泗水方言,被子)、草席直接在堤上的条石上睡。说起条石来,一百多斤的石头,赶上两个你沉了。祖父说着,用食指点了点我的脑门儿。 我点了点头嘟囔着,那还怪沉来。 那个石头全靠人去打,打得四四方方的,錾子都直冒火星子。还得运到堤上,还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垒。桥基也全靠人工去挖,先把河道清干净,把淤泥一锨锨的“呼”出来,“呼”出山一样的土方,用小平车推,用筐挑,用排车拉,用麻袋装,硬生生用手将几百米的河道桥基清理出来,可费劲了。 那你们怎么不用挖掘机啊?我扭过头去,天真地看着祖父。 祖父哈哈大笑,露出仅剩的几颗牙来。刚吸进去的烟从他嘴里鼻子里忽地蹿了出来,呛得他佝偻着身子咳嗽起来没完。当他抬头来的时候,黝黑的脸已涨得通红:哪有挖掘机啊,手扶拖拉机都很少。那时候星村还是公社化管理,基本上一个公社顶多也就有两三辆拖拉机,还得各个大队轮换着用。拖拉机少,畜力也不多,驴啊牛啊现在没有养的了,那时候有几头驴几头牛也全都拉来修渠了。最主要还是靠着人力,春秋还好,天气凉快,干活干得也快,夏天太阳毒,热晕倒好几个,冬天又冷,在冰冷的泥汤子里浆鼓(音。泗水方言,劳作)那滋味儿真的是不好受。 那不会不修这个渠了吗。我不屑地问。 祖父摇了摇头说,庄稼离不了水,特别是咱们这山又多,地势也高,雨水存不住,河水流不到,就这么一条河有时候还断流呢。这条渠修好了,就能将水引到咱们这来,等旱的时候,上游一放水,咱们的庄稼就有救了。活再难,总得有人干不是?那时候人的积极性不敢想象,手磨起水泡来了,挑了水泡接着干;格勒拜子(音。泗水方言,膝盖)磕破了,裹上破布一样干;胳膊扭伤了,用酒搓一搓继续干。这渡渠建成,可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受利,你父亲,你,甚至你的子子孙孙,但凡是离不开土地的,都将受益于这条渠。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祖父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眼里仿佛闪着光,比那晚的星星还亮。祖父还在说着,我却早已昏昏沉沉地睡去,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我这个从未真正经历风雨的小孩子又怎会体会得到呢。等我醒来,已经回到了祖父的老屋,睡倒在他油亮的凉席上。我早已将祖父的话抛在了脑后,但我与红旗渡渠,已经有了解不开的羁绊。 伟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趟风冒雨,泥地里打滚儿,河水里立桩;他们自己设计,自己测量,自己管理;他们坚定地与自然作斗争,驯服洪水猛兽,鬼兽旱魃。于是红旗渡渠在一声声的号子和飘扬的红旗里,在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辅助下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其建设难度和审美设计,丝毫不亚于全国其他水利工程。它与北干渠上的愚公渡槽、换新天渡槽等其他渡槽一齐打通了华村水库与各个乡镇的脉络,为星村公社乃至整个泗水县的耕地与民生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它们是愚公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是红旗精神、敢叫日月换新天精神的完美诠释,是劳动人民驯服水患与旱灾的有力手段。 后来祖父在一个夏天故去了,在一个红旗渡渠开闸放水的日子里故去。那一辈参与建设红旗渡渠的人们也所剩无几了,他们完成了属于那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共眠于奋斗了一生的土地里。可红旗渡渠仍岿然不动,继续为我们甚至我们下一辈输送着宝贵的水源。 但红旗渡渠,那个庄重又严肃的老者,仿佛也渐渐地追不上时代的车轮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渡渠的作用似乎逐渐没有那么重要了,红旗渡渠的名字也逐渐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就是根据它的桥洞数量而得名的二十孔桥。 他们也会老吗?他们也会有完成自己使命的那一天吗?我想会的,可他们从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会有人用真挚的笔触去记录他们,去歌颂他们,去纪念他们。红旗渡槽,或许也从来不需要刻意去为它歌功颂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座丰碑,一座独属于劳动人民的丰碑。 二十孔桥 红旗渡渠是祖父的故事,二十孔桥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接下了祖辈、父辈的接力棒,在新时代履行我们的使命与担当。 二十孔桥,此时成了红旗渡渠与渠下那条河共同的代名词。 二十孔桥河水流量从来不大,只有三个桥洞有水流过,甚至有时候会断流,但这丝毫不影响乡人对这条河水的热爱。妇女们喜欢在桥洞子下洗衣服,穿过桥洞子的风总是能吹散所有的劳累与烦躁;孩子们可不懂什么诗意,脱光了,趴在桥洞子前边冲刷出来的小坑里露出头来,叽叽喳喳地打闹嬉戏,于是河水边泛起了一片白沫儿,倒像是天上坠落的云彩。 二十孔桥的青春期属于夏天。河边的草丛郁郁葱葱,偶尔有白色的蝴蝶飞来,落在开出蓝花的鸭跖草上。柳树的根须,贪婪地伸进水里,扎出些乳白的水根来;河底的水藻伸出长长的触须,蔓延成绿色的云雾,在河底自由地招摇着;乱七八糟的石块,仿佛就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没有任何过度的修饰,没有刻意的布置,一切都是自然的样子。 拿一支鱼竿,甩进桥下的小水坑里,能钓出手掌长短的白条,肥胖的厚子,披着蟒纹的乌鱼,金黄色的鲫鱼来。或下挂网,便能捕着手指大小的麦穗,泛着彩光的鳑鲏,细长的河虾。到了枯水期,则露出一片小的沙滩,偶尔冒出几个小气泡,我总是想着下边会藏着些生灵。于是扔掉鞋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去,用手沿着气泡冒出来的地方掏下去,有时候运气好了能摸出“科彭”(音。泗水方言,河蚌、沙拉蛤等淡水贝),小的和沙子一个颜色,泛着黄绿色的光,大的长着些薄薄的青苔;运气不好,掏出来一些破衣裳烂泥,用劲儿大了,一屁股坐进泥里,回家不免又得挨一顿揍。 二十孔桥是我们孩子的海,是大人们的避暑胜地,是庄稼的天。 直到我们上了初中,二十孔桥忽然变了模样。 河畔堆满鸭粪鸡粪牛粪,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味。柳树枯死,闷头倒下,树皮脱落,露出干枯的根。草丛如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变得暗淡。粪水沿着枯草流进河里,河水因含着过量的微量元素导致蓝藻繁殖爆发而发绿,水面漂着一层油污,塑料垃圾袋、泡沫随处可见。二十孔桥的水,变成了一潭死水,一潭散发着臭气毫无生机的死水。 我愤恨,惋惜,焦灼,不停地在河边踱步,如同河边翻着白肚皮挣扎残喘的小鲫鱼,瞪着眼睛盯着黑压压的天空。忽然一声闷雷,打破了沉寂,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一场暴雨突如其来,试图冲刷着肮脏的一切,我折返回家,无奈得只能叹息。 我回家向父亲痛诉着我看到的一切。父亲也撇着嘴摇头破口大骂,这不只是咱一个庄的问题,往北还好几个庄呢,靠一个庄去管,根本管不了。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在全国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长制的任务。河长制也在泗水县全面实行,二十孔桥有了专人管理,由各大队第一书记直接负责。同时县政府指导环保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十孔桥的水质进行检验测量以及对星村镇各个养殖场进行指导与管理。 彼时我正上高中,父亲在家包了几十亩地,又养了几十头猪。忽然有一天,一辆白色轿车停到了我们家门口,车上下来三个身着白衬衣的人。一个面皮白皙的年轻小伙子手拿文件夹,一个三十来岁的手低头摆弄着胸前的执法记录仪,另一位年长者与我父亲交谈着。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他们是环保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派下来走访调研的同志们,我竟有些期待与拘束,我知道二十孔桥有救了。 泗水县山多丘陵也多,耕地有限,所以大多数都经营着些养殖的副业,这不失为一个发家致富的好道路。我们村有十几家养殖户,几乎全都集中在二十孔桥和北岭附近。养殖场废水的随意排放,是二十孔桥河水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乡亲们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并不觉得排放废水是污染环境的做法。但他们抽取二十孔桥河水冲洗圈舍,然后又排放到河里的行为,使得河水里的有机物质超标,造成水里蓝藻疯狂繁殖;粪便里残留的兽药、消毒液,严重危害水里的生物多样性。这确实是影响二十孔桥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因。 乡亲们的生产生活,又离不开水,离不开二十孔桥。生产生活与环境保护,仿佛成了不可调节的矛盾。 但县里调研的同志们不这么认为,几个大队的书记也不这么认为。他们没有选择“一刀切”的工作方法,没有强制关停这几家小型养殖场,而是积极地为农户出谋划策,解决问题。我亲眼看着同志们挨家挨户调研取样,整理数据。尽管有些农户并不理解他们的行为,认为只不过是上边来找事的,甚至有些人认为是来要钱的。但他们耐心地向农户们解释,讲述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们钻进布满蜘蛛网、满是粪水的圈舍,指导着圈舍的改造工作,汗水打湿了他们的衬衫,蜘蛛网也爬满了他们的头上,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积极地配合工作。 我悄悄地问那个年轻的小同志,你们是党员吗。 小同志抬起头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他咧着嘴笑着跟我说,是啊,今年刚入的党。他笑起来露出雪白又整齐的牙,额头上有一抹擦汗擦出来的黑乎乎的烂泥。他的白衬衫已经被汗塌透(泗水方言:湿透),紧紧地贴着皮肤,隐隐约约能看到他白皙又瘦弱的脊梁。他挽着袖子,胳膊上沾着点点的干透的黑泥。裤脚湿乎乎的,分不出什么颜色来。 其他的两位同志也是一样,污泥在他们身上开出了大大小小的花。 忙到下午,一行人聚集到了党员活动中心。安排落座后,我随着父亲坐在第二排的中间位置。大队书记在台上主持会议,年长的同志对农户养殖场的改造与整理也提出积极的建议。我印象最深的几条,首先就是将传统的露天堆肥改造成为半封闭式的蓄粪池,这有效地解决了粪水随着雨水流进河道而污染水源的问题;另一项就是清洗圈舍需要配备污水处理器,几家养殖场可以合用一个,将废水统一收集处理,既节约成本,又解决了废水的处理问题。我不由得赞叹,这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实际、最有效、最省钱的办法。 会议结束,已近黄昏,大队书记悄悄地安排了酒水饭菜,欲留下调研团的同志们。三位同志连连推辞,只提出要去二十孔桥上看看。 夕阳西下,调研团的同志们和大队书记、养殖户们站在二十孔桥上,远眺着河水,露出了欣慰的笑来。河水缓缓地向南流淌,夕阳照在二十孔桥上,“红旗渡渠”四个大字闪着金色的光。我们期待着二十孔桥的重生,这是我们祖辈辛苦换来的青山绿水。保护环境,正是我们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我回头看去,猛然看到一面红旗,从一家养殖户的棚顶,缓缓升起。远处芦苇丛里,游出两只野鸭子,在水面画出一串句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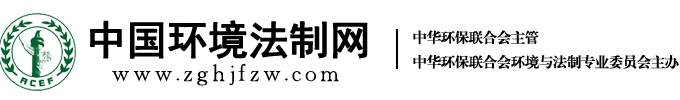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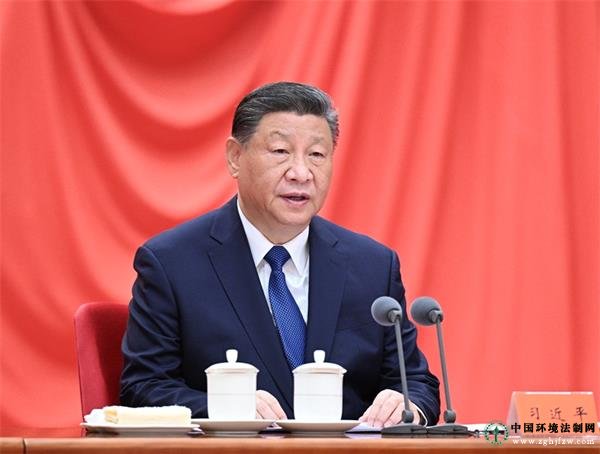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