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信用制度已经被中央确立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如何顺应全球绿色发展时代的要求,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从2019年“两山理论”发源地之一的浙江丽水开始生态信用体系创新实践,本人有幸主持了相关项目,2023年国内第一个生态信用学术组织——北京信用学会生态信用专委会成立,到今年四部委《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印发,“生态信用”首次进入国家政策的工具箱。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过20多年的纵深推进形成的强大正外部性,使其成为“公地悲剧”等生态环境负外部性内化的对冲机制成为可能。而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性、生态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碳市场产品的虚拟性,则是生态信用制度源起的内在需求和必然逻辑。 生态信用体系特殊之处在于:一是基于制度性需求。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产品由生产定义,生态文明时代的产品由需求定义,如绿水青山;二是源于系统性增信。由生态信用主体承诺,由政府、机构和平台背书增信形成。例如,碳信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国家自主贡献(NDC)等就是国家信用背书的特殊资产。也不同于当下作为约束机制的“环保信用”制度。生态信用将信用应用场景从公域规制拓展到价值创造层面:生态价值实现、生态资本生成和绿色溢价降低,尤其是成为金融资本向生态资本转化的新支点,从而实现生态环境领域“信用有价”。 简而言之,生态信用体系是由生态环保领域信用主体承诺,由政府、市场和平台背书增信形成的生态资源保护、生态价值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等系列生态信用机制。 生态信用体系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创新的成果,首次将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人与人”信任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阶段。在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市场、科技、金融等路径之外,能否蹚出第五条社会治理的路径?在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能否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发展的公共产品和中国贡献? 生态信用,值得探索。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中心研究员、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兼生态信用专委会主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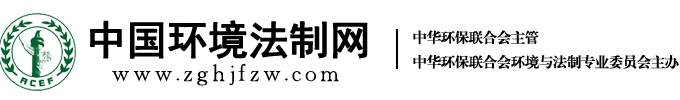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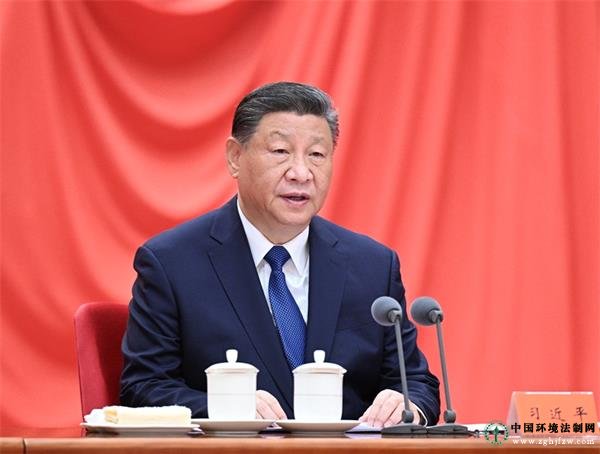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6702号
